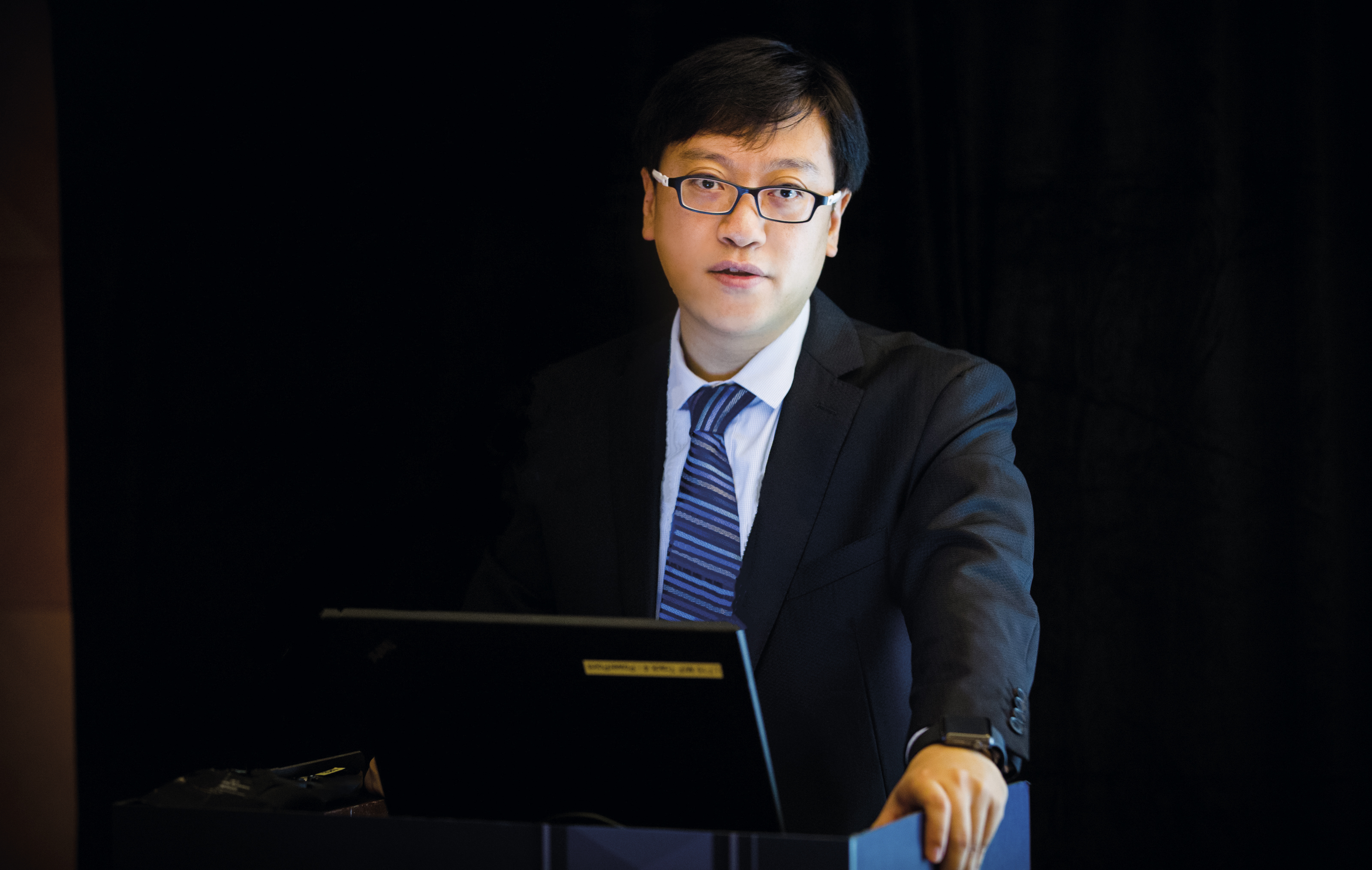
(图注:明明在香港策略会路演现场)
“我研究生涯中,最大的变化是从政策到市场。”谈及作为首席经济学家的AB面,明明总结道。
2015年,明明离开供职七年的中国人民银行(下称“央行”),入职中信证券做固定收益分析师。同样是研究货币政策、流动性、利率、汇率等领域,但视角从政策转向市场。这年他34岁,事后一个同事跟他说,35岁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,应该考虑做些改变。
在明明看来,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市场研究各有千秋。前者关注人口、气候等中长期范围内的大课题,并且需要考虑政策执行过程如何平衡复杂的社会利益,当成功处理好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件,会令人有莫大的成就感。后者作为商业研究,核心是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,不可避免地更多关注短期问题,但及时直接地反馈也让人领略市场的魅力。
正式离开央行之前,时任老领导与明明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。老领导说,你不应该走,但你离开之后,要做政策和市场之间沟通的桥梁,把政策的实际情况向市场解释清楚。明明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,除了日常解读政策动向,他还写了几本书,其中一本介绍中国的货币政策,还有一本介绍全球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。
2022年,明明的市场研究生涯和政策研究生涯变得一样长,都是七年。他发现,自己现在不仅在向市场解释政策,也承担着很多帮助政府了解市场的工作。“近两年接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后,参与了很多决策机构的会议,大量工作都与此相关。”
说起七年市场研究生涯,明明坦言前两年比较辛苦,也曾经把自己累进医院。但提起工作细节,他很喜欢用“有意思”来形容。在他看来,路演很有意思,跟海外投资者解释中国经济很有意思,研究别国央行也很有意思。他不赞同社交平台上极端勤奋的“鸡汤”,“休息不好怎么工作?提高工作效率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可能是更重要的。”
以下为本刊与明明的对话:
研究生涯AB面:从政策到市场
问:宏观研究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?
明明:我2008年进入央行工作,那一年印象最深的是大家中午一起在食堂看奥运会,然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。2008年上半年,央行是一个月加一次准,下半年是一个月降一次准,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那时候刚参加工作,还在跟着处长学写签报,对金融危机感受比较懵懂。后来回过头看,2008年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拐点。
金融危机前,全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稳定增长,特别是欧美国家,一直认为找到了经济发展的要领,就是所谓的金融自由化和市场经济。过去发达国家认为,东南亚、南美等区域发生金融危机,是因为它们不够自由,不够市场化。没想到,被认为最自由、最市场化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。
在这之后,大家发现可能整个宏观和金融的学术框架都要发生变化。比如我们当时研究的资本自由流动,IMF(国际货币基金组织)以前一直认为资本应该完全自由流动,金融危机之后,它也承认资本不能完全自由流动,完全自由化带来的过度投机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。
时至今日,宏观经济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,比如2008年之后,全球的零利率和低通胀的问题;比如今年为什么又出现了高通胀,这些都是未来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。
我认为这就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奥妙,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,而是开放性的,你必须有自己的理解。
问:如果将你的研究生涯划分为A面和B面,你会如何去定义?
明明:我的研究生涯的AB面应该是从政策到市场,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变化。
我2008年进入央行,工作了七年;2015年到中信证券,今年正好也是七年。在央行做政策研究,这是A面,进入中信之后,做市场研究,这是B面。
问:在你看来,政策研究的核心是什么?
明明:政策研究和市场研究有很大的区别,但不能说谁高谁低,主要是二者出发点不同。
政策研究很多时候站位比较高,看得比较远,它面临一个很关键的课题是,怎么去平衡复杂的社会关系。
举个例子,央行要不要降低存款利率?存款利息是很多老百姓的收入,特别是低收入人群、老龄人群,定期存款收益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。存款利率一降,他们的收入就下降了。
另一方面,我们的工商企业又面临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,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,需求不足,要稳增长肯定要降低利率。很多政策设计它其实是在处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。
当然,从事后来看,这个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降息或者不降息能够解决的,它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政策组合。对于短期经济的压力,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降低利率,但是对于很多人养老或者是他的收入问题,我们更多要做第三支柱,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养老理财就是第三支柱。
目前来看,政策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。过去我们面对的更多是国内问题,现在面临的是国际和国内的双重问题,国际上有俄乌冲突、全球能源价格上涨,国内又叠加地产下行周期等等。
未来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还会更加复杂,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处理新问题,但政策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此。
问:从政策研究转到市场研究,你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的?
明明:这个过程确实不太容易。
首先是心理定位上需要转变。某种意义上说,央行是整个金融市场最大的“甲方”,很多时候是“约谈”金融机构,而证券公司是市场上的中介服务机构,我们跟金融机构见面叫“上门路演”,得看人家的时间合不合适。我想从央行离开的小伙伴多少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。
体制机制上的差异也比较大,过去在央行的时候,跟着处长干就可以,我工作了七八年还是处里年纪最小的,领导还叫你小伙子。刚来公司的时候固定收益研究团队还没有完全搭建好,我还要同步组建团队,培养新人,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工作。
在工作方式上,分析师研究形成观点之后,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传播观点。例如,我们认为8月MLF(中期借贷便利)可能缩量,我们要如何向市场传播这个观点?疫情之前,这个传播主要靠双腿跑,上门给投资者讲。来到中信之后,我一个月出的差,比过去在央行一年的出差还多,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跑。
2017年前后还累病过。有一段时间出现反复低烧,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肺感染。一个老大夫跟我说,小伙子,你这病在旧社会叫痨病,这都是码头上扛麻袋的工人得的病,累的。你这年纪轻轻怎么就累成这样了?
当然,现在回过头来看,那个时候对于工作的理解还不够到位,也做了一些无用功,浪费了很多精力和体力。职业的转换可能两年左右是一个坎,2018年左右,研究团队搭建好了, 工作上形成了一套方法论,慢慢就好起来了。
问:站在当下,你会如何看待研究生涯中的A面和B面?
明明:从A面转向B面之后,我感觉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,其实是从B面又回到A面。
当年离开央行的时候,在老领导的办公室跟她深谈了一次。她说,你不应该走,但是你离开之后,要做好政策研究和市场研究之间的桥梁。这两个世界的沟通很重要,真正做过政策的人才懂政策,才能把政策讲清楚。你到了市场之后,要讲一些真实客观的情况,不要去渲染市场情绪。
金融市场有时候是受情绪影响的市场。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,当大家都预期会大跌的时候, 可能会陷入“市场下跌-预期悲观-市场继续下跌”的恶性循环。这时候很多政策也可能被曲解,大家会倾向于放大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当然,我现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向政策解释市场,现在突发的复杂事件越来越多,决策层也亟需了解一线的情况。比如俄乌冲突了,市场是什么反应?站在市场机构的角度,我们怎么看?决策机构需要知道市场的看法,才能知道如何设计政策能够稳定市场预期。
最近两年,尤其是接了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后,经常会参加一些决策机构的会议、调研,也包括参与学术界的一些讨论,更多地承担起双向沟通的责任。
做研究,兴趣和效率更重要
问:与政策研究相比,市场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?
明明:市场研究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
从研究方式上讲,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,但是它会把一个具体的问题拆解得非常细致。当初我们研究国际资本流动,看到过一篇中国香港的报告,把国际收支表和结售汇的数据都写得非常细,我们一看就认为确实研究做得非常独到。
从出发点来讲,市场研究的核心是商业研究,说白了要为投资者创造价值,这点跟政策研究很不一样。我记得离开后跟央行的小伙伴们聊天,他们开玩笑说,你们就老写房地产、金融危机什么的,也写点“一带一路”这些的东西啊。我就说这个题目确实很好,但很多还是概念层面的,短期内没办法帮助投资者赚钱。
对市场研究的考核逻辑也不同,分析师的业绩每个季度要排名,每年算总账,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研究需要关心短期的事情,比如本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做了多少?CPI是多少?社融表现如何?这些具体问题对投资业绩有直接影响。
市场对研究成果的反馈也比较直接,这个月你看对了,你的业绩好,大家就给你点赞;你看得不好,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水平也就这样。有点像一个江湖一样“快意恩仇”,这就是市场研究的魅力。
问:有分析师可以一直看对吗?
明明:这其实是一个怎么去做市场研究的问题。
首先,没有人能够未卜先知。如果有人能永远对的话,那已经超越巴菲特了,完全可以自己去做投资。
其次,金融市场上大家其实是在交易不同的信息,而分析师的优势在于客观中立。至少在机制上,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。我自己不投资,不存在利益冲突,我就是面向所有投资者,客观陈述自己的观点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,看错了怎么办?在这方面市场其实也很包容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专业投资者,他们更在乎你的思考逻辑、分析框架。他们对市场有自己的判断,之所以愿意听分析师讲,其实是在验证自己的观点。
另一方面,市场研究是一个外向型的工作,分析师要尽可能跟更多人聊,包括企业、政府、市场、外资、内资等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,所以我们的信息集合可能是最大的,投资者需要通过我们来补充外部信息。
问:做市场研究七年,是什么让你保持热情?
明明:市场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丰富和多元化,你每天能见到的东西非常有趣。
比如有一年去美国出差,美国那边接待的同事是个墨西哥人,一路上跟我吐槽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不好,抱怨他在美墨边境修墙。去旧金山的时候,当地同事指着金门大桥说,美国修一个大桥可能十年都修不下来。也是去了华尔街才知道,因为租金太高,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多半是对冲基金,共同基金和一些老牌银行都在西海岸。
这些内容都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重要素材,没去过很难有这种感受。比如每次看到美国就业数据,我就会想起那位墨西哥裔同事说墨西哥人都在美国餐厅里打工,进而考虑到公布的就业数据中是不是不包括新移民?
作为一个宏观研究员,你的视野要宽广,信息要足够丰富。这样在研究的时候,才会有很多鲜活的想法。如果一个分析师从来没去过菜市场,不知道老百姓吃什么、买什么,对通胀的研究可能容易得出非此即彼的极端结论。
出去之后,我发现很多海外投资者非常了解中国。比如我曾经跟美国一位非常资深的基金经理交流,一开始我讲中国的GDP、CPI,她听完之后直接说“nothing new”,没啥新意。我就换了个主题,给她讲中国的县域经济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城投平台,讲相对贫困的地区为什么也能建设这么多高速公路。讲这些的时候,我发现这位“挑剔”的客户一直睁大眼睛,认真地听着。讲完出门的时候,当地的同事跟我说“You are one of the best”。
问:你认为自己哪些特质对研究而言是比较重要的?
明明:我对新鲜的事物比较感兴趣,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比如我虽然离开了央行,但对各国央行一直很有兴趣。过去海外出差的时候,只要有当地央行的行程,我当天就会很兴奋,话会变得特别多。每个国家的央行都有自己的特色,比如泰国央行原本是一个王子的宫殿,里面陈列了很多的佛像,我当时发朋友圈说,这可能是全世界最“佛系”的金融机构,非常有意思。后来,我把这些年海外出差的见闻都写进了一本书,一共八章,每章讲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,也包括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沿革,应该说是我个人感情投入最多的一本书。
我不太认可社交平台上的一些“鸡汤”,某某名人早上6点起床跑步,开完一天会头晕脑胀晚上还要大量阅读,看很深奥的书。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,大家都是正常人,休息不好怎么工作?提高工作效率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可能是更重要的。
(编辑:张静)


